
作者 | Elise
编辑丨腾宇
题图 | 《大考》
见到谢爱磊,是他刚从清华大学完成演讲回到学校的第二天。他自认是典型社恐,但聊起他研究的课题,就会滔滔不绝。他的朋友说他是大学教授里的异类,因为他所研究的课题实在过于小众。
自2013年起,谢爱磊对中国四所顶级大学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小镇和农村。他们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一书是谢爱磊这项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他在过去十年对农村和县城考上顶级大学的“小镇做题家”进行追踪研究,用丰富的数据与事实,客观呈现小镇与农村学生如何调整身心,适应大学的过程。
书中还原了“小镇做题家”在社会舆论偏见遮蔽下的真实境遇,揭示了寒门学子面对的残酷现实与他们的应对方法。有读者把这本书比喻为“小镇做题家的圣经”,也有读者说,如果自己能早一点看到这本书就好了。

《小镇做题家》
谢爱磊
上海三联书店,2024-5
接受《新周刊》的专访时,谢爱磊也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谢爱磊同样是“小镇做题家”的一员,有与被调研学生相似的困境和疑问。这些经历沉淀成他对出身相仿的年轻人的关切,才引出了后来的研究课题。
除了个体本身的处境,研究同时涵盖了从农村教育困境,到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再到“小镇做题家”的心态、探索和反身性思考。他还提到了社会各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措施,希望营造一个公平、包容的教育环境,让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特点得到充分发展,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以下是谢爱磊的自述:
“小镇做题家”并非擅长做题,
而是只能依赖做题
我是农村来的孩子,父母都是农民。个人成长经历让我对农村学生特别关注。在我的成长中,有两个印象特别深的故事。
一个是我从初中上高中那年,第一次到市里面去,我几乎一整个学年都不敢讲话。因为初中读的是村里的学校,所有人讲的都是当地方言,包括老师。到市里读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意识过要讲普通话。因为没讲过,不敢讲,身边有同学一直以为我是个哑巴。
另一个是,当年高考,我在一所省重点里考了文科第一,但我不知道怎么填志愿,父母无法给我有用的建议。我不知道自己的分数已经足够上最好的大学。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希望当一名老师,于是在报志愿时填了华东师范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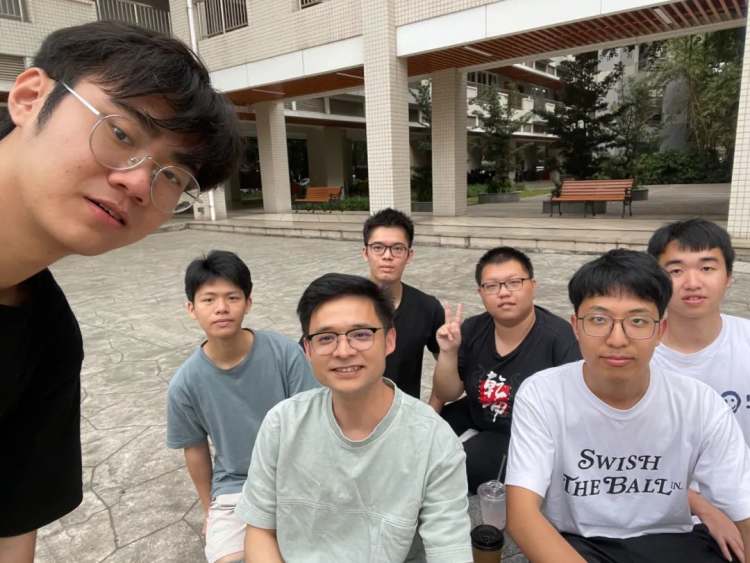
前排中间为谢爱磊。(图/由受访者提供)
这些经历都促使我后来思考:农村的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哪些问题?我想多做一点研究,去讲这些人的故事,去为像我一样遭受过压力和困扰的社会群体做些事情。
2013年,我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还没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但有“凤凰男”“扶弟魔”之类的称呼。我认为这些词都有污名化的嫌疑,对农村学生群体其实是不公平的。当你看不到故事全貌,把眼光盯在少数极端个案身上时,很容易形成偏见。
我一直在反击这些“偏见”。我从农村来,知道在农村孩子身上发生过什么。农村的孩子能不能够走出农村和小镇,考进精英大学,除了个人努力和智商影响,其实还有很多社会的因素。如果不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讲出来,他们不会得到特别有针对性的帮助。于是我前后花了十年对他们进行跟踪研究,写成了《小镇做题家》这本书。
“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最早来源于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是少部分从农村或小镇出来的优秀大学生用来自嘲的词语。他们出生在农村或者小镇,擅长做题,从小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通过高考获得成功。好不容易考进名校,这群“做题家”才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还隔着一道长长的鸿沟。
我其实一直不愿意把这些学生称作“小镇做题家”。因为“做题家”这个标签,人们理所当然认为他们是擅长做题的人。事实恰恰相反,农村学生其实更难成为擅长做题的人。比起城市的学生,农村学生缺乏优质的教师、优质的教育资源,获得高分的难度显然会更大。这从我国重点高校里面农村学生的比例也可以看出来。

(图/《大考》)
“小镇做题家”并不擅长做题,而是他只能依赖做题。当你看到一些人自称“小镇做题家”的时候,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人擅长什么,可能是缺少点什么。长久以来,他的人生里面只有“应试”一个单向度的人生赛道,正是这种单一,让他在适应大学的生活或者拥抱更加广阔的人生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
我每次访谈都会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依然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吗?”他们从上大学那一刻开始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开始他们会告诉我“也许吧”。到了大四,他们有的会说,“光有文凭肯定是不够的,你还得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这四年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做到。”
你会发现,有的学生意识到在社会上求职没那么简单后,会变得更加理性。但是对于很多农村的孩子来讲,肯定是期待上一个重点大学改变命运。因为,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跌跌撞撞,也是一种成长
在进入异质的、被主流话语体系定义为更高阶的文化中,农村和小镇青年往往要承受沉重的心理和情感代价。
这正是“做题家”自我叙事背后的基本逻辑——“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它不是一种客观能力叙述,而是社会流动中个体的一种生存心态,喻示了或稍轻、或沉重的心理代价;它也是阶层跨越者的一种独特探索,包含了一些新奇、迷茫和无力;它又是一种对人生成长经历的反思,是处于社会流动中的农村和小镇青年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社会化过程以及教育经历的反身性思考,而它蕴含了改变的力量。

(图/由受访者提供)
从心态、探索与反身性思考三个维度看,“小镇做题家”都是可以自定义的。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不打算去定义这个词。也就是说,我提出一个理解“小镇做题家”的线索——心态、探索与反身性,以方便大家认识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但至于他们的心态、探索与反身性究竟如何,则留给他们自己去定义。
为了能让他们能够实现“自定义”,在这本书里我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在写他们的时候,舍弃了学者们喜欢做的“深入分析”。书的主体就是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并用他们自身的语言来表达,让故事作为主体,去呈现和定义他们自己是谁。
我想表达的是,尽管“小镇做题家”受过去的认知图式的限制,但当他们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个体其实是有能动性的。虽然这些“小镇做题家”看起来像陷在命运的泥沼里出不来,好像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把控;但实际上,当他们开始思考,就已经在和命运抗争了。

(图/《鸣龙少年》)
我写这本书,是希望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小镇做题家”是一种难以摆脱的一种状态。他们在讲自己的这个心态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精英大学缺乏“游戏感”,第二个方面是容易自我低估。关于“游戏感”有个例子。有一次,在访谈中,学生突然问我:“老师,你有没有考虑过,城市和农村两个世界有什么不同?”他接着说:“我发现城市的路跟农村的路、小镇的路,其实是不同的路。村子里面的路就是用来走的。在城市里,路是可以用来玩的。”
小镇和农村学生跟城市学生比起来,可能因为家庭生活和教育经历的原因,在大学里面可能很难迅速适应和融入新环境。他们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会“跌跌撞撞”,但“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收获。我希望让他们意识到,“跌跌撞撞”也是一种成长。
研究者不应该有上帝视角
我认为,起跑线是客观存在的。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无名的人》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里边有一句歌词,我用在书上的标题:“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想,这也是我成长经历的写照。
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保持一个学者的姿态,高高在上,提出观点,结合数据,把受访者的经历打散,按照理论需要把分析和结论讲出来;另外一种就是放弃这些分析,站在学生的角度去写作,把“小镇做题家”的经历、遇到的困惑,原封不动呈现出来,不代替他们做分析,那么这些故事就是最鲜活的。

(图/由受访者提供)
我选择了后者,现在看来有点大胆,也怕专业的研究者无法接受,但我总想,研究者不应该有上帝视角。
这些成长经历会激发他们很多特别的思考,而我在看着他们在成长。成长意味着你能够在大学里面通过你的经历获得自主性,能够自如地在社会上立足,判断哪些东西适合自己,哪些东西不适合自己。你获得你的自主性,自洽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目标,它应该让我们能够主动地应对不确定性,探索怎么样拥有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
媒体常说,“小镇做题家”作为阶层跨越者,更容易产生“中产焦虑”。其实你换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会发现,中产的焦虑其实是中产的“特权”。像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余秀兰说的,中产如果在焦虑,说明他还抱有一点希望,他想去让孩子维持自己的状态。也有人说,小镇做题家到了中年就回归均值了。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信号,起码说明他们在跟命运搏斗。

(图/《追光的日子》)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每一个人都在成长,每个人都在试着在跟自己和解,每个人都在试着自洽。“小镇做题家”背后总有一些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外在的力量在在驾驭他。如果说不清楚这件事,可能会导致对别人对这个群体的“受害者有罪论”。
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社会的背后的结构性力量,理解“小镇做题家”的处境之后,再去评论,而不是评判。我希望大家了解了这个群体以后,可以意识到“小镇做题家”并不是在说他们擅长什么,而是在说他们心里觉得缺乏什么。作为教育者,需要把欠缺的东西给他补上去,让他可以去拥抱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这是教育要做的事情。
运营:嘻嘻 排版:段枚妤

评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