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最后一天,当人们在商业街或广场等待跨年的时候,作家郑在欢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同进入了胡同里的蓬蒿剧场。在这个隐秘的地方,他要开一场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对于图书的售卖来说,这是一个惯常的流程。以往的这类活动,大多以作家对谈为主,严肃、正经,有时甚至是尴尬。郑在欢对这种固定的形式多少有些抗拒,他觉得,让人感受文本魅力,远比那些解构的内容更有意义,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在一两个小时的谈话里,悟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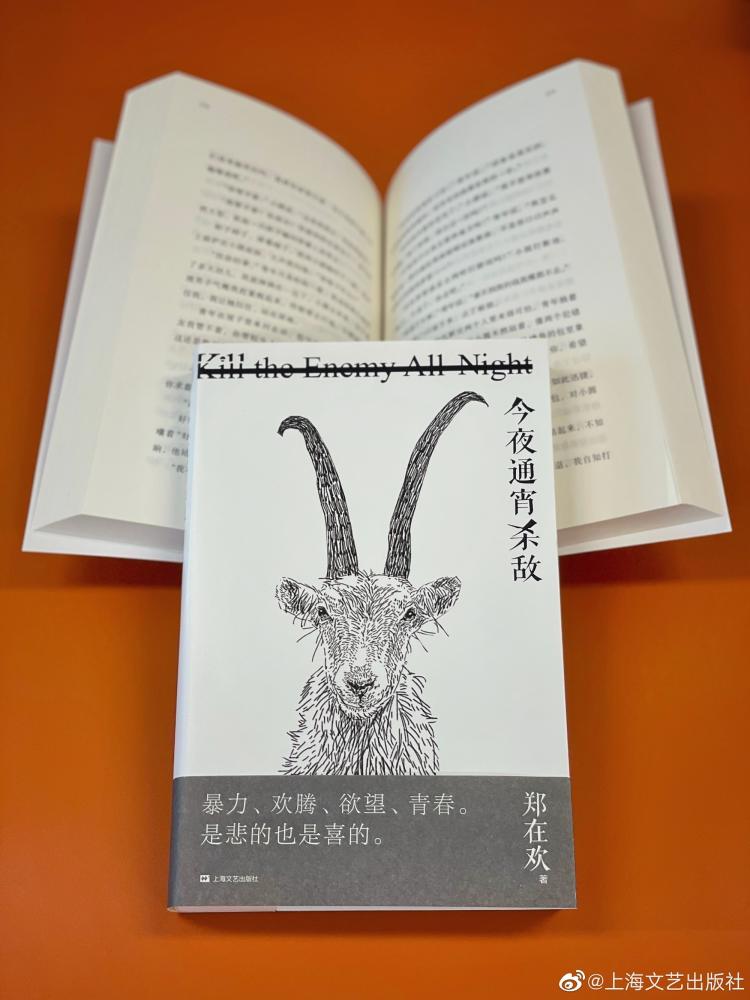
郑在欢新作《今夜通宵杀敌》。/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所以在那晚的活动上,郑在欢也没有和那些来自文学圈的朋友谈论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只是轮番地去阅读新书《今夜通宵杀敌》里的片段,读完之后,再和场下的观众聊着每个人所独有的通宵故事。
其中有一个女孩的分享让郑在欢记忆犹新。女孩说,自己曾经在跨年夜坐火车跑到郑州去见一个心爱的人,但那个人并没有出门见她。那天凌晨,饥肠辘辘的她,吃着从车站附近买来的蛋饼,又买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票。她知道,等抵达的时候,迎接她的将是下一个晨曦。
如果是在小说中,这个故事无疑是俗套的,但当一个真实的人面对面讲述时,故事的质感就变得不再一样。在郑在欢看来,这就是语言在现实语境中的魅力。在这背后,有互动,也有共情,而这些,正是文学所追求的。

2021年12月11日,作家郑在欢与导演王红卫、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一起就他的新书《今夜通宵杀敌》展开了一场对谈。/微博@单向街图书馆
除了与读者交流,郑在欢的小说还联结了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这场跨年秀开始前,他们每天都会在一起排练,他说:“大家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能和我打心眼儿里欣赏的人玩在一起是特别美妙的事情。”
而这些朋友,也让喜欢摇滚乐的郑在欢圆了组乐队、当主唱的梦,起码在那晚,他很尽兴。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哼唱过周杰伦,长时间听过刀郎,也模仿过许巍。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他经常会把磁带的后半截扯出来,录上自己唱的歌。他觉得,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八成都是喜欢文艺的,当时的流行文化也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他说:“其实‘娱乐至死’也挺好的,但前提是高质量的内容。”
“自己写得不爽,小说就没意思了”
郑在欢今年32岁,和同龄作家相比,他的职业生涯是比较长的。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去年年末接续出版的这两本书,其中大多的篇目也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完成的。
写下这些故事那几年,他在北京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他待在出租屋里,床上堆满了书,消磨时间的方式,除了饥不择食似的阅读,就是一天看4部电影,等入睡时,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在郑在欢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当时觉得,长篇作品才能算作一本书,而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才能有出名的机会。

作家郑在欢。/受访者供图
但坚持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无处发表,出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煎熬的日子里,他靠写一些短篇故事来调节自己的心绪。渐渐地,他发觉,好像这种形式的小说也很有魅力。
他写下的第一篇叫《这个世界有鬼》。那段时间,人们都在关注着富士康员工跳楼的社会新闻,郑在欢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一篇与此相关的简短报道。报道里写,三个少年相约去自杀,最后,两个人离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郑在欢以此为原型,写了这篇小说。在写那位幸存者时,他如是写道:“李青出院之后受到了各方关注,记者堵在他的出租屋里,反复问着他同样的问题。他只用一句‘活得太累’敷衍他们。他们给他请了心理医生,面对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只能说自己‘喜欢活着’。”郑在欢说:“我写小说,并不是想把故事讲成那种社会调查,我想追求的是,把一件事儿说得有趣、丰富而有弹性,如果写得太俗,或者我自己写得不爽了,小说就没意思了。”

郑在欢作品《团圆总在离散前》。
等到24岁,郑在欢觉得自己在北京实在是待不下去了。他在那个夏天考虑着,要不干脆回到老家做个农民算了,“与乡邻生活在一起,出门就能互相打招呼”。但等到真正回到故土,他发现,自己已经难以再适应那样的环境了。他说:“回去的时候,见不到年轻人,每天只能和大妈们、老太太们聊天,每次聊的也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蚊虫叮咬,生活单调,驻留了5天,他毅然决定,要回到北京。
这次回京,他写了一篇名为《驻马店女孩》的小说。这个短篇故事,也像是他在重新审视自我的身份。他在当中写道:“很多次到达这里,又坐上火车匆匆离开。身为一个驻马店人,我只是驻马店的过客。”写完这篇,他找了一份影视公司的工作。通勤与熬夜,成了他生活里最主要的两件事。在现实的挤压下,小说成了一个忽远忽近的幻梦。
“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绑定在一起的”
对于如今的郑在欢来说,北京是盛放自己躯体与精神生活的地方。但在十几年前,这个城市之于他的意义,只是打工糊口的目的地之一。与媒体口中在顺境中成长起来的90后不同,郑在欢的生活经历充满了波折。
他的生母早逝,他由奶奶带大。因为继母不愿支持,他在读完初中一年级之后,就没再接受过学校的教育了。打工,成了他谋生以及逃离的唯一出路。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追随亲戚到保定的白沟镇生产箱包。每天早上六点到夜里十一二点,他都是在踩缝纫机中度过的。那时,他身边的人,大多与他相似——年龄小的,十五六岁,稍长一点,也不过二十岁出头。难得休息的时候,一群人混混日子,上个网,也就过去了。

真正的好文本是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图·pexels
郑在欢觉得,时间长了,这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又辗转余姚、宁波等地,寻找新的出路。但工作是看不到头的,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批,也依旧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下班后,有时和同事一起上网、打麻将,有时靠读书来打发时间。
那时流行韩寒和郭敬明的作品,他看了之后,觉得他们写的东西好像和自己生活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他开始试着写下自己身边的人的故事,满街晃悠的辍学少年、留守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小孩、溃败的中年人,都成了他书写的对象。写完之后,他发现,快乐好像也多了一点。
2009年,他认识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一家淘宝店,店面大、生意忙,急需人手。于是,这个朋友联系了他。就这样,郑在欢在海淀的西山脚下当起了淘宝客服。但干了几天他就放弃了,一方面是因为他打字慢,并时常出现错误;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刚开春的北京,风刮得很大,每天坐在工位的时候,他能感觉到脚下的风在乱串。生活里没有什么熟识的人,再加上气候的寒冷,让他觉得自己很凄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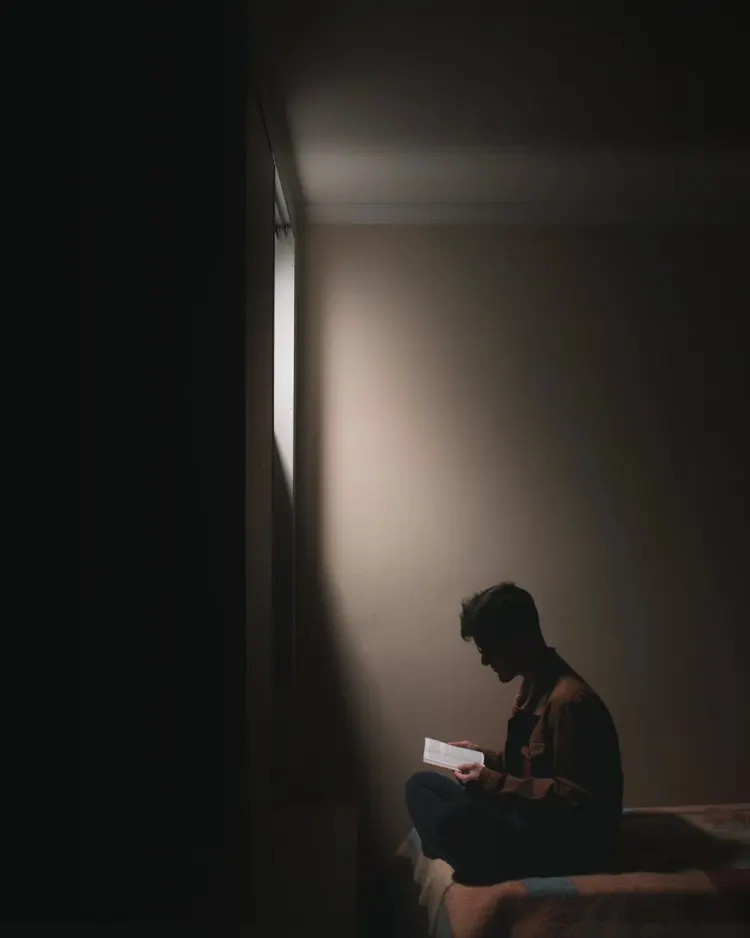
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图·pexels
也同样是在这年,他的生活迎来了一线转机,他偶然看到了小说征文比赛的消息,首奖30万元。他用手机打字,投出了一部玄幻小说与一部流浪冒险小说,最后流浪冒险小说得了奖,奖金8000元。写作这部小说时,他认识了第一个文学上的朋友魏思孝。在郑在欢的记忆里,魏思孝戴着发箍,家里摆放着的都是小众出版物——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
19岁的郑在欢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或许可以走写作这条路。在聊天的过程中,魏思孝提到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例子。郑在欢当时有些不屑,他心想,看书就看书呗,咋还追星呢?但后来读到那些代表作的时候,他也就理解了。
不过,在文学上,郑在欢一贯如此,他从不想去做一个苦大仇深、满嘴理想抱负的文学青年,他只希望,自己能写一点儿有意思的东西,至于高尚、崇高的那些追求,最好可以在故事里被消解掉。
很快,他把奖金当作自己写作的启动资金,买了一台电脑,带着一股“莽劲儿”,投身于写小说当中。他格外自信,身边的几个人也都在鼓励他,这更让他觉得,只要能把自己想写的内容落在纸面上,就一定能有所成就。

19岁的郑在欢不清楚文学是什么,他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或许可以走写作这条路。/图·pexels
结果事与愿违。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参与到一些带着目的性的写作当中,甚至拮据的时候,为了7000多元的稿费,他还想过和几个朋友一块儿攒一本书出来。他说:“现在回看,那些文字的价值,仅仅是赚钱活下去的工具。”在他心里,真正好的文本,是和生活绑定在一起的。他再翻阅那些故事时,也时常会回到一段段被别人视作挫折与坎坷的经历里。他觉得,好像也没那么苦,偶尔也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
离开故乡,才能重塑自己
2017年,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出版。有不少人都通过这本书,认识了郑在欢。媒体、读者、图书编辑也都给他打上了一个个标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都与驻马店这个小城相关。
郑在欢说:“我澄清过无数次,我从来没有一刻钟想过给自己弄一个什么文学故乡,都已经是‘地球村’了,把人局限在同一个地域上,在艺术领域是很偷懒的一件事儿。”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霸权,就好像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文学上的靠山,从而获得了独家解释权。

郑在欢作品《驻马店伤心故事集》。
纵观文学的历史,有很多作家都被这样的话语模式框定住了。譬如,提及福克纳,必定会说到约克纳帕塔法;谈论马尔克斯,马孔多这个小城也一定不会缺席……人们往往也就遗忘了,这些作家写过的地方,不只有自己的故乡。
在郑在欢眼里,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他说:“当我们还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模式都会受到家庭和故乡的影响。”不久前,他和朋友闲聊,他说自己不喜欢吃奶奶做的面条,因为奶奶给他盛的面很少有汤,“就像个面坨”。但他爱吃的,是面汤多,同时漂着香油和菜叶的那种面。朋友反问他: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突然意识到,奶奶在故乡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在她的观念里,面汤是骗人的玩意儿,扎扎实实的才是好的”。
郑在欢说,这就是家乡对一个人的塑造,但离开了那里,我们身上的烙印也就没有那么重了。“无论是小说还是生活,我都希望自己能做个‘地球人’,更大、更开阔,因为只有甩掉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们才能重新塑造自己。这应该是一个人的理想。”

在郑在欢眼里,故乡是一个人的来处。/图·unsplash
而至于为什么还愿意书写故乡,郑在欢的答案是“十几岁时候的生命体验对人的刺激很强”。他说:“涉世未深的人,是敏感的,接触什么都是全新的,虽然整体上是波澜不惊,甚至有些枯燥,但身处其中,会发现,青年时期出格的表达、不顾后果的行动,都是纯粹的、有诗意的,并且值得分享出来。”
当他来到北京之后,他觉得,大家都挺文明的,发于情,止于礼:“没有多少能看清的东西能刺到我,如果我在当中,我或许想要去揭开它,但我要是游走在外面,我也只能是远观,这或许也是我的城市书写少的原因。我的城市生活不够透亮。”

评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