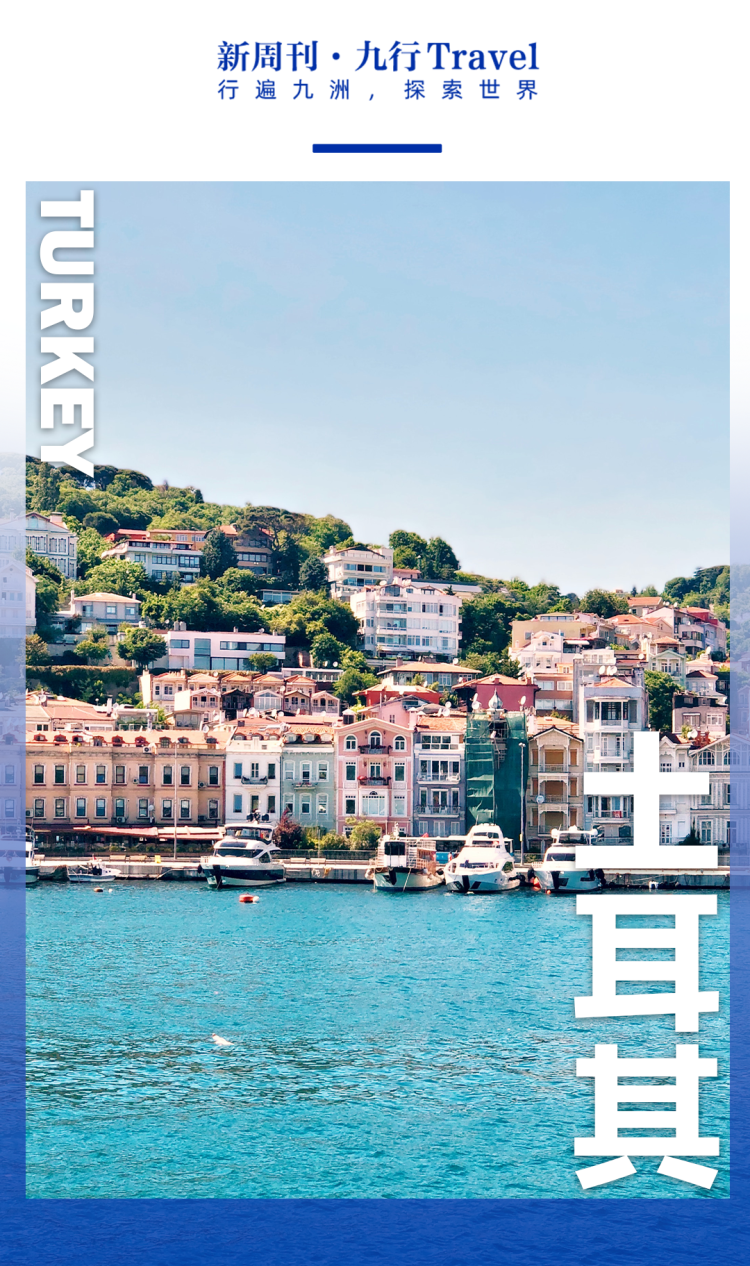
前些天,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出境团队游第三批名单,土耳其在列。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名单公布后,土耳其旅游旅游咨询量上涨超过10倍。
去土耳其的经典路线,是直飞伊斯坦布尔,再转机去卡帕多奇亚乘热气球,去棉花堡泡温泉。
但你其实,也可以像欧洲人那样,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找一个海滩待着。

△安塔利亚以绿松石般的海水著称。(图/Unsplash)
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安塔利亚省,是土耳其第二大热门旅游目的地,深受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青睐——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把这里列为7月到10月的首选度假地点。
盛夏里的悠长假期,湛蓝的土耳其滨海往往会被挤成春节时的三亚。但与这里热闹、开放的景象相悖,土耳其的产业、经济趋于冷清、保守——跨国企业被赶走了,这意味着,你提前看好的酒店也不一定存在了。
大假时节,
英国人和本地人的“海陆空争夺战”
爱丁堡市飞往安塔利亚市的航班满座了。先前跟我安静对眼神打趣的小洋娃娃,终于在接近目的地前号啕大哭,伴随着高分贝尖叫。身旁的老爷爷以浓重的高地口音跟我表示抱歉:“我几乎每年都来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度假,爱死了这边的大海和海边的古希腊、古罗马废墟。但这次要遭罪了,因为我把老老小小三代共十三口人全带来了。”
这让我想起去年看的那部非常喜欢的英国电影《晒后假日》。影片讲述的是一对英国父女在土耳其地中海的度假经历,阳光明媚、海水湛蓝,却气氛深沉、情绪伤感。孤家寡人的我也试图“戏精”上身,陷入帕慕尔用来形容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情绪。

△土耳其的海滨景色。(图/Unsplash)
然而,这里是温度宜人的地中海,落地后的喧嚣热闹,伴随着海风的气息,立即让我兴奋起来。我在朋友圈写道,重归欧洲两个边缘后,英国让我放松,而土耳其才真正让我松弛。
正如冬天的海南省会变成“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三亚区”,盛夏的土耳其滨海,会变成“英国伦敦市安塔利亚郡”。
大量皮肤通红的盎格鲁—撒克逊度假客,自东向西,塞满从安塔利亚市到博德鲁姆市(Bodrum)的酒店客栈及沙滩躺椅,抓紧时间进行对他们至关重要的“光合作用”。

△《晒后假日》剧照。(图/网络截图)
维基百科上说,土耳其的英国人人口在3.4万人到3.8万人之间。由于有大量居民和度假者,费特希耶-欧鲁丹尼斯海滨(Fethiye-Oludeniz)在2007年被《泰晤士报》《卫报》评为世界最佳旅游中心。
有超过7000名英国公民永久居住在费特希耶,每年夏天则有约60万名英国游客到访这里。《晒后假日》的故事发生地和取景地,正是位于费特希耶东南部的欧鲁丹尼斯小镇。

△《晒后假日》剧照。(图/网络截图)
电影里1999年的度假样貌,与今时今日并没有太大差别,除了手机替代了DV。片中的度假酒店里,因为父亲“社恐”,女儿只好独自上台唱卡拉OK,荒腔走板地唱起R.E.M.乐队的名曲《失去一切信念》(Losing My Religion)。
而我刚在费特希耶满布廉价泳池旅馆的城郊住下,街对面的酒吧就传来难听的卡拉OK,是英伦摇滚第一名曲——Radiohead那首《怪胎》(Creep)。好几十桌英国酒客高声喧哗,等待轮到自己的台号,像极了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卡拉OK轮桌唱。

△费特希耶的酒吧里,挤满了英国人。(图/张海律)
将滨海度假小镇塞成沙丁鱼罐头的,远不只远道而来的英伦客。古尔邦节的到来,加上学校开始放暑假,让土耳其人夺回了属于自家的主场。
接近欧鲁丹尼斯海滨的公路,已经塞成了数公里之长的停车场。作为滑翔伞天堂,小镇的天空也快被五颜六色的帆布堵严实了。
因为注定赶不上在夏日每天11点离港的轮船一日游,我索性钻进空调劲吹的旅行社办公室,打探还有没有去往附近著名海湾的船只。毕竟,拥挤着过来后没着落的游客还有很多。
“以前肯定有,现在,船长们累到罢工了!”旅行社姑娘告诉我。看来,我不只是春节去了三亚,还相当于五一到了淄博。
那间旅行社办公室对面,就是《晒后假日》里父女俩所住的泳池酒店,一点都不时髦,和电影里一样老旧。

△《晒后假日》里,父女俩所住的泳池酒店。(图/张海律)
我在吧台点了一份烤肉,一个小伙过来介绍自己,他是同样累到罢工的滑翔伞飞行员。“以前,我每天能带四五个中国人飞伞。现在,旺季过去快两个月了,但几乎见不到你们中国人。不是开国门了吗?你们都去哪了?”
“航班还很少,国际机票也贵。即便你当场决定复工,我也舍不得玩滑翔伞。”我对小伙说道。头一天傍晚,从最为热门的度假小镇卡什(Kas)到费特希耶的大巴上,我碰到两个中国学生。她们告诉我,最近在土耳其见到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是趁放假出来的留英学生,一并被列入英国航班的到客数字。
在Booking订好的客栈竟然不存在
早在疫情前的环球旅行时,大概是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那些年,我就切身体会到“去全球化”的趋势。

△土耳其马路上的巴士。(图/Unsplash)
这集中表现在,在很多中小城市,谷歌地图再也查不到公共交通信息,而非得用本地开发的App。这倒也没错,不让跨国公司独大,转而支持本土科技企业。只是,这就让手机旅行变得没那么方便了。
此次飞抵安塔利亚市,当晚要去东面滨海历史名镇西代,我提前通过一款App预约了一趟凑满乘客才发车的机场大巴。相近城市之间的交通方式,已恢复到需要通过客栈问路、抵达车站查班次的非智能手机年代。
幸好,土耳其公路客运发达而可靠,一般不会有到车站后车票售罄的倒霉情况。城内和区域公交,大多就得找报刊亭购买本地通勤卡(要付工本费),免不了回到口袋里得有现金甚至硬币的从前。

△西代古城的阿波罗神庙。(图/张海律)
更为独特的“去全球化”感受,出现在抵达预订的旅店时。
在卡什,大假时的青旅八人间床位费飙升到50欧元一晚,还订不上。我通过Booking订了代姆雷(Demre)一间没有评分的客栈。下了客车,拖着行李,跟着导航走到那里,眼前是一座亮着灯光的两层小楼,旁边是一座清真寺。楼里有正在用晚餐的一家子,男主人让我进屋,看着我手机上的房源地址,纳闷道:“没错,是我这儿,但我没开客栈和民宿啊!”
幸运的是,这个叫穆特鲁的男人是当地一名中学英语老师。他拨打客栈预留电话,号码不存在,而客栈的名字“Huzurlu Bir Konaklama”,实在不像一个正常客栈会取的。
“这是‘平静归宿’的意思。”穆特鲁说。莫非旁边清真寺里的墓园,就是“平静归宿”?

△代姆雷景观。(图/Unsplash)
穆特鲁带我到附近那些作为度假屋的独栋木屋和便利店打探,大伙儿也都对这个“平静归宿”毫不知情。谷歌搜索各种关键词,也没有半点踪影。显然,我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电诈”。
给英文客服打电话,对方表示抱歉,立即给我退款,并让我改订附近一家快捷酒店。奇怪的是,酒店显示有房源的,点进去却不可预订。穆特鲁打电话过去确认,房间充足,直接来就行。在穆特鲁家吃完饭,这个新朋友把我送到酒店,并让我游玩之后跟他再约。
对了,代姆雷是圣诞老人(St.Nicholas)的老家,圣诞老人是一千多年前当地一位喜欢给孩子发糖果的东正教圣人。十多年前我碰到的时任土耳其驻华大使曾抱怨:“是可口可乐公司把他绑架到芬兰的!”
这么说,穆特鲁就是我的“圣诞老人”吧。

△位于安塔利亚市近郊、建于古罗马时代的阿斯班多斯剧院(Aspendos Tiyatorsu)。(图/Unsplash)
几天后,在非旅游城市穆拉(Mugla),我又一次用Booking预订,抵达后一样找不到房源。
附近一家酒水超市的伙计不会说英语,帮我打了电话过去,才知道商户早就不用Booking了,但没有下线,也没注意到我的预订。
“要不去我妈妈家,带大花园。但要一个小时车程,我得夜里12点才能来接你。”电话那头说着解决方案。我当然没法答应,只能让酒水店主帮忙订了城郊另一家商务酒店。

△卡什安静的一角。(图/张海律)
后来才得知,4年前,因为抽成和税点问题谈不拢,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想扶持本国科创企业,Booking就和土耳其“脱钩”了。
我在Booking上能查能订,是因为用的是西班牙流量卡,但只要连上本地Wi-Fi,页面就是一片空白。而我去的地方又实在小众,爱彼迎和其他平台的房源都很稀缺。
我很好奇,土耳其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因为有多家本土平台的存在,Booking就没了市场。穆特鲁给我推荐了三个网站,但在大假时节,一样没有多少高性价比的房源。他自己和家人度假时,是直接给相熟的店家打电话预订的。
日趋保守的国度
作为某种程度上的“老土”,我已有9年没有回访这个算得上熟悉的国度。
安塔利亚市和费特希耶市之间,奔驰在最美海岸公路D400上的客车,会经停很多小镇,晒成古铜色皮肤的俊男靓女不停地上上下下。这时候,窗外是湛蓝的海天一色,眼前是无敌的青春气息。
到了海滩上、游艇上,更是琳琅满目的比基尼风景。到了爱琴海一侧,在博德鲁姆市(Bodrum)那座公元前4世纪建成的古希腊剧场里,夏夜时永不落幕的流行和摇滚演出,更是把滨海翻腾成如伊比萨一般的派对岛。
直至游船上偶尔上来一些戴头巾的中老年女性、沙滩上掠过身着布卡罩袍的影子,我才意识到自己正身处一个这些年从世俗化掉头、回归保守传统的国度。

△安塔利亚老城的黄昏。(图/张海律)
从欧鲁丹尼斯乘坐小巴返回费特希耶的路上,我在山林间的幽灵村镇卡亚科伊(Kayaköy)下车,沿着长满青苔的狭长青石板路,掠过几百座住宅废墟,走向可以眺望村落全景和大海的山脊线。
这是一座为了躲避海盗,由希腊定居者开辟的城镇,在希腊语中名为“Leivissi”。它在20世纪初的人口规模达到顶峰,曾有2000多户家庭、6500多人居住于此。“一战”的希土战争和随后强制执行的人口交换,让这个镇子人去楼空。1957年的一场大地震,又倾覆了剩下的一切。后来,也有地产商想介入,试图对考古遗址进行商业开发,但一直没见动静。

△山林间的幽灵村镇卡亚科伊。(图/Unsplash)
走到村庄核心的东正教教堂废墟,我才意识到,今年不就是希腊土耳其人口交换100周年?1923年1月30日在瑞士签署的《洛桑协议》,让这对“世仇”迅速执行强制驱逐令。土耳其交出120万名希腊裔,换回了希腊的40万名土耳其裔。
几年前,我在希腊东部一座小城见过一位年届百岁的老奶奶。老奶奶出生于土耳其,婴孩时被希腊裔父母带回希腊。经历过人口交换的那一代人,还活着的已经寥寥无几。
如今一百年、四代人过去了,虽然希腊人热衷于追看奥斯曼宫廷剧,但两国的“世仇”关系并没有多大好转。最后一批还保留故土记忆的人早已离世,他们的后辈不大可能愿意“常回家看看”,因为那不再是属于他们的家园。

△希腊人离开后的卡亚科伊。(图/张海律)
几天后,在爱琴海海岸的度假名城博德鲁姆,我进了一家数字游民咖啡馆。午餐时间,叫来外卖的男主人让大伙放下手头的活计,边吃边聊。
餐桌前,有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教物理学的波兰女博士,有美国的韩裔小程序开发者,有到处旅居躲避兵役的俄国青年。从俄乌冲突到法国抗议活动,大伙儿的话题越聊越深。作为短暂过客的我,提及先前去过的幽灵村落,以及百年前的希土人口交换。
“今年还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呢。”咖啡馆男主人说道。“可我们变得越来越退步、保守。”

△博德鲁姆远眺。(图/Unsplash)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电影里那样的女儿,我早前试图“戏精”上身的这趟“晒后假日”,还是以男人们热衷却无济于事的政治话题作结。这样也好,深入情感,让人愁苦;指点江山,让人假嗨。
有2500年历史的古希腊剧场,传来人气歌手西拉(Sıla)结合突厥节拍和摇滚编配的歌谣《美人》(Afitap)。
“让我们给自己算命吧,难道还要听朝圣导师的吩咐?写下过多少希望的承诺,朋友们一道看看吧。”让人坐不住的韵律,跃出剧场,经过海边的骑士团古堡,顺着晒后的海岸线,一路东征。
编辑:谭山山
校对:邹蔚昀
排版:邱邱

评论
下载新周刊APP参与讨论